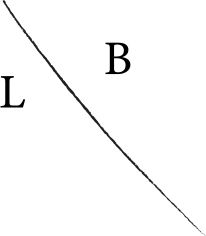陶之化石
青年陶艺家陆斌及其陶瓷作品
李砚祖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著名艺术批评家
文章发表于《新艺术家》2004、9
化石是自然界的一种造化,指那些在地质历史中经自然界作用而保存于地层中的古生物遗体、遗物以及它们的生活遗迹。陆斌的“化石系列”作品不是用陶仿制化石,而是试图采用陶的形式将当代人类的生活“物化”或者说“化石化”,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揭示生活以及生活的真实存在,用陆斌自己的话来说,即“企图站在一个未来的时态回顾今天的现实,用琐碎的生活细节来描写今天的生活”。事实上,陆斌作品的内在意义和作品的自在言说远不止这些,它既是一个现代陶艺家对当代生活的描述,又是陶艺家自身对艺术、对生活乃至对人生的一种反思,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言,反思总是哲学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中国哲学简史》,第一章)。
在这之前十余年的陶艺学习和创作,其整体追求,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即“唯美”,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大学生,经受了改革开放之后现代派艺术思潮的洗礼,克莱夫·贝尔的名言“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成为艺术学子和艺术家们的信条,并影响到他们的艺术创作。陆斌在回顾自己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时写道:“现代主义是强调美的,有意味的形式与材料本体语言的表现,这同陶艺的特性有着天然的契合。现代陶艺对于材料的关注以及材料在烧成过程中可控或偶发的变化,对于抽象形体变化的敏感,都使它便于与现代定义的审美理想获得沟通。”(陆斌:《石头记》)正是在这种对艺术对陶艺的理解之下,他创作了一系实用花器以及名为《砖木结构》系列和《墙系列》等作品。
从二十余件《砖木结构》的系列作品来看,陆斌试图追求和表现的重在陶的语言和结构本身,“砖木”只是结构和形式的表象。为《砖木结构》之17至21这五件作品的组合,这些类似劳动工具的器物,创作者并不关心其是否是一种工具的镜象,而关注的是组成这种工具外形的结构形式,关注的是不同结构所展现的陶的语言和要素。其他《砖木结构》的作品都表现了这一共同的趋向和追求,即注重形式,除了形式还是形式。其后,他还创作了《活字系列》等一批唯美主义的作品。
陆斌 1988 年毕业于南京芝术学院的陶艺专业,与 80 年代的大多数艺术青年一样,他也曾在现代主义的集体狂欢中,经受过西方现代形式主义艺术的洗礼。这个时期陶艺界的关键词是反叛和语言。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是否可以这样说:反叛传统的作为工艺美术的陶艺,建立一种表现性的,个人标识性的.以形式的创新为主要目标的新的陶磁语言,是这个时期的热点和焦点,现代主义强调美的、有意昧的形式,强调美的规律和语言本体与陶艺有着天然的契台。陶艺本身对于材料的关注,对于抽象形体的敏感,对于超脱于具体的生活意义之上的细微韵致的把握,都使它便于与现代主义的审美理想获得沟通
物极必反。当专注于形式、为形式而形式从而走到极端之时,敏感的艺术家将会日益怀疑这种探索的真实性和必要性。其时,陆斌也感到,现代主义的审美理想已不能完全满足和表现自己对创作内涵和深刻性的追求了。数年深圳特区生活的体验、精神上的彷徨迫使其重新审视陶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新的表现方式。在这种徘徊中他意识到必需要有一种新的转折和飞跃、要有一种对现有形式的背离与否定,才能获得艺术创作的新生。
在现代陶艺中,将器物的口等部位封死,使日用之物成为非日用之物,成为“雕塑”,其作者首推日本的陶艺大师八木一夫。不过,陆斌的创意似乎走得更远,他认为自己的这些创作,是尝试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与作者艺术追求之间的有机关系,对这些中国文化符号的借用,并非仅出于对传统文化的依恋,而是确信这些文化符号所折射出的现实内容,这些内容无疑揭示出作者陶艺创作的指向及其时代生活的某些侧面。从观赏者而言,也许能读到更多的东西,或者说赋予其更多的东西。深圳学者老道在《浮世守夜者》一文中论及陆斌的作品时写道:“陶冶是一种修为,陆斌因此积习宿命般的认真。陶的艺术对于此时的人生忽然有了一种庄严和责任。在《都市系列》里,那些来自火热熔炉,如今却被冷却的‘俗物’,反衬出从艺者良医和祭司的心地。《都市系列·煲》里隐匿着的男女生存结构,把温情脉脉的补晶酿成两性的祭器。”这类释读也许是创作者的预设,也许是观者的阐释之言。但无论如何,《都市系列》中红黑两色的《煲》、尸布缠身的《年年有余》和漫无指向的《指北针》,都蕴涵着作者对前阶段陶艺创作注重“形式之美”的反叛而走向文化与哲学深处的思索。这一阶段的探索应作为陆斌《化石系列》作品创作的前奏。